作者:西地那非
2025.08.28首发于第一会所
字数:10832
写在开篇:
【边看边学?这才是男人该追的历史小说!】
【尘封史册之外,曹阿瞒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魏武猎艳录》是情色小说,亦是严肃历史。
本书以《三国志》、《后汉书》为骨,以合理想象为血肉,深入汉末宫廷与
战场,力图还原一个全面、立体、有血有肉的曹操。
他的霸业与他的欲望,本就一体两面,共同谱写了这段传奇。
在这里,您不仅能见证官渡的烽火、赤壁的东风,更能窥见金市的珠喉、帐
中的温存。
这一切,都是理解那个时代与那个人的钥匙。
读稗官野史,习正经国史。
一部小说,双重收获。
【本故事为闲余创作、额外连载,更新与否,皆在诸君之间。若您喜爱,恳
请点赞、评论。助力,点赞越多,更新越快!诸公,请助孟德一臂之力!】
【历史背景导读(建宁七年冬,公元174年,洛阳城外)】
皇帝:此时的皇帝是东汉的汉灵帝刘宏。
他是个贪图享乐、昏庸无能的皇帝,非常信任和依赖身边的宦官(太监)。
宦官集团:以王甫、曹节为首的一群大太监,把持着朝政大权。
他们权势熏天,陷害忠良,卖官鬻爵,无恶不作。
皇帝对他们言听计从。
受害者:士大夫(清流官员与太学生):许多正直的官员和读书人(太学生)
痛恨宦官祸国殃民,被称为「清流」或「党人」。
他们试图铲除宦官,但失败了。
关键事件:大约6年前(公元168年,建宁元年),大将军窦武(外戚,皇帝
的岳父)和太傅陈蕃(德高望重的老臣)这两位清流领袖,联合起来谋划诛杀王
甫、曹节等宦官。
可惜计划泄露,窦武、陈蕃反被宦官诬陷谋反,惨遭杀害,他们的家族也被
灭门。
这就是震惊天下的「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开始。
此后,宦官对清流的迫害就没停过。
曹操此刻:曹操(字孟德),当时只有20岁。
他的家乡在谯郡(今安徽亳州)。
他被当地官府推举为「孝廉」(汉代选拔官员的一种资格)。
他带着一位重要官员——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桥玄的推荐信,刚刚抵达
帝国首都洛阳的郊外。
他怀揣着年轻人的热血和抱负,准备踏入这个由宦官掌控、危机四伏的政治
中心寻找机会。
正文开始
第一卷:初据兖州 第一章:洛水寒刃
【建宁七年(174年)冬,洛阳城外】
曹操以孝廉身入京,持太尉桥玄荐书,冀入仕途。
是时,宦官(王甫、曹节等)势炽,权倾朝野。
雒阳城的风似裹了冰碴子,抽在脸上生疼。
我勒马洛水桥头,玄色大氅灌满了北风,猎猎作响。
桥玄公的荐书在怀中滚烫,孝廉之名,不过踏入这龙潭虎穴的敲门砖罢了。
抬眼望去,雒阳城阙如蹲伏的巨兽,灰蒙蒙的宫墙压在天际,透着一股子陈
腐的腥气。
「孟德,雒阳水深,慎之,再慎之。」桥公临别之言犹在耳畔。
我曹孟德年方二十,血是热的,骨是硬的,岂惧这潭浑水?嘴角扯出一丝冷
峭,靴跟一磕马腹,乌骓马长嘶一声,踏碎洛水薄冰,直向那帝国心脏奔去。
甫入城,血腥气便混着尘土味扑面而来。
朱雀大街不复传闻中冠盖云集,反倒透着一股死寂。
行人瑟缩,商户半掩门板,唯有一队队执戟的北军士卒,甲胄森然,踏着整
齐而沉重的步伐巡弋而过,铁靴踏在青石板上,发出令人心悸的闷响。
他们的眼神,鹰隼般扫过街巷,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压迫。
「闪开!王常侍车驾!」尖利如阉鸡的嗓音骤然撕裂沉闷。
街面瞬间清空,人群如潮水般惶恐退避,匍匐于道旁。
我勒马避入巷口阴影,冷眼看去。
只见数十名身着绛红缇骑服的宦官亲卫开道,簇拥着一辆金顶朱轮、饰以鸾
鸟的奢华安车,车帘低垂,看不清内里人物,唯有一股浓烈得刺鼻的熏香弥漫开
来。
车驾之后,竟拖曳着长长一串囚徒!男女老幼皆有,粗麻囚衣褴褛,颈套重
枷,脚系铁镣,在寒风中踉跄前行,每一步都留下暗红的血印。
鞭子如毒蛇般不时抽下,皮开肉绽的闷响和压抑的哀嚎令人齿冷。
「渤海王刘悝谋逆,奉旨,阖族弃市!」一个领头宦官趾高气扬地宣告,声
音里透着残忍的快意。
渤海王刘悝?先帝亲弟!我心头剧震,一股寒意从脊椎直冲头顶。
谋逆?何等荒谬!不过是王甫、曹节这些阉竖清除异己的惯用伎俩!看着那
些被拖向刑场、面如死灰的宗室贵胄,看着他们眼中孩童懵懂的恐惧和妇人绝望
的泪水,我攥着缰绳的手背青筋暴起,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这就是我大汉的雒阳?这就是我立志要匡扶的朝堂?金碧辉煌的宫阙之下,
流淌的竟是如此肮脏腥臭的血!
「嗬…嗬…」一个白发老翁踉跄跌倒,枷锁砸地,发出刺耳的声响。
旁边一名缇骑狞笑着扬起鞭子,眼看就要落下。
「住手!」一声断喝自我喉中迸出,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
乌骓马受惊,前蹄扬起,长嘶震耳。
那缇骑的鞭子顿在半空,连同周围所有目光,齐刷刷射向巷口阴影中的我。
惊疑、审视、还有一丝被冒犯的阴鸷。
领头的宦官眯起细长的眼,上下打量着我这风尘仆仆的外乡人,嘴角扯出一
个皮笑肉不笑的弧度:「哪来的狂徒?敢阻王常侍法驾?活腻了不成?」他尖细
的嗓音像钝刀刮过骨头。
我深吸一口凛冽的寒气,压下翻腾的杀意,在马上略一拱手,声音沉冷如铁:
「谯县曹操,蒙桥太尉举为孝廉,初入京师。见老弱踉跄,一时情急,惊扰常侍,
还望海涵。」
「桥玄」二字,被我刻意咬得清晰。
那宦官听到「桥玄」名号,眼中阴鸷稍敛,但倨傲不减,冷哼一声:「哼,
原来是桥太尉举荐的孝廉郎。年轻人,雒阳城的水,深着呢。管好你的嘴,还有
…你的手!走!」
他不再看我,尖声催促队伍。
鞭子终究没再落下,但那老翁也被粗暴地拖拽而起,留下一道更长的血痕。
车驾与囚队在压抑的死寂中继续前行,唯有铁链拖地的哗啦声,如同地狱的
丧钟,一下下敲在人心上。
夕阳如血,将巍峨的南宫门阙染成一片凄厉的暗红。
我驻马朱雀阙前,望着那象征着至高皇权的巨大门楼,白日里那囚徒颈上枷
锁的沉重、孩童眼中凝固的恐惧、宦官脸上那令人作呕的得意,还有那弥漫不散
的血腥与熏香混合的怪味,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啃噬着我的心脏。
「此间宫阙…」我低声呢喃,声音被寒风撕碎。
一股比洛水更刺骨的寒意,混杂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灼烧肺腑的野望,在胸
中疯狂滋长。
这金玉其外的煌煌帝都,内里早已是蛆虫横行的腐肉。
桥公的「慎之」言犹在耳,但此刻,我只觉一股暴戾之气直冲顶门。
慎?在这虎狼之地,唯有权柄与力量,才是活命、才是主宰的法则!我要撕
开这层虚伪的锦绣,我要…染指这至高的权色!
「当染吾色!」最后四字,如同从牙缝中挤出的铁屑,带着血腥的决绝。
指甲深深掐入掌心,刺痛传来,却远不及心头那团烈火的万分之一。
暮色四合,风雪更急。
我按着驿丞的指点,策马出了雒阳南门,沿着覆满薄雪的官道行了约莫半个
时辰,才在洛水一处荒僻河湾旁,寻到那处破败的官驿。
几间土坯房在风雪中瑟缩,门前一盏气死风灯昏黄摇曳,仿佛随时会被寒风
掐灭。
驿卒是个佝偻的老吏,须发皆白,脸上沟壑纵横,堆着世故又卑微的笑,将
我迎入唯一一间还算完整的厢房。
「曹孝廉受累了,受累了!这雒阳城里的驿馆,早被那些个…咳,贵人们塞
满了,只能委屈您在这城外将就一宿。」老吏一边哈着腰解释,一边麻利地拨弄
着屋内一个呛人的炭盆,试图驱散那刺骨的阴冷。
土炕冰凉,墙角结着蛛网,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劣质炭火的烟气。
「无妨。」我解下大氅,随手扔在炕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目光扫过这陋室,白日里朱雀阙前的滔天怒火与野望,此刻被这现实的破败
与寒冷一激,反而沉淀下来,化作一种更沉郁、更尖锐的东西,在胸中左冲右突,
亟待宣泄。
案上有一壶劣酒,我抓过来,拔掉塞子,仰头灌了一大口。
辛辣的液体如同火线滚入喉中,灼烧着冰冷的脏腑,却压不住那股邪火。
老吏察言观色,浑浊的老眼在我年轻却紧绷的脸上转了几圈,又瞥了一眼我
腰间佩剑,脸上那卑微的笑容里,忽然掺进一丝心照不宣的暧昧。
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带着浓重的市井气:「孝廉郎初来乍到,白日里又
受了惊,这长夜漫漫,天寒地冻的…可需寻个暖脚的,解解乏气,驱驱晦气?」
我握着酒壶的手一顿,抬眼看他,目光锐利如刀。
老吏被我看得心头一凛,腰弯得更低,却仍陪着笑:「小老儿不敢欺瞒,这
驿馆虽破,却也…咳咳,备着些『官中』的体己。
都是干净人儿,懂规矩,知冷暖。」他特意加重了「官中」二字,手指隐晦
地朝雒阳城方向指了指。
官妓?王甫、曹节那些阉狗爪牙掌控下的玩物?白日里那奢华安车中飘出的
浓烈熏香,与眼前这破败驿馆的霉味、劣酒的辛辣,还有老吏口中「干净人儿」
的暗示,奇异地交织在一起,猛地在我心头点燃了一把邪火。
一种强烈的、近乎亵渎的冲动涌了上来——撕碎这虚伪的「干净」,践踏这
由阉竖把持的所谓「官中」体面!
「哦?」
我放下酒壶,声音听不出喜怒,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剑柄,「唤来。」
老吏如蒙大赦,脸上褶子都笑开了花:「好嘞!孝廉郎稍待,稍待!」
他佝偻着身子,飞快地退了出去,脚步声消失在呼啸的风雪声中。
屋内重归死寂,唯有炭盆里偶尔爆出几点火星,映着我阴晴不定的脸。
窗外,北风卷着雪沫,疯狂地拍打着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嘶鸣。
约莫一炷香后,门轴发出艰涩的「吱呀」声。
老吏推开门,一股更猛烈的寒气裹着雪花卷入。
他侧身让开,一个单薄的身影被推了进来,随即门又被迅速关上。
来人是个女子,约莫十六七岁年纪,身形纤细,裹着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
丁的粗布旧袄,下摆短了一截,露出冻得发青的纤细脚踝。
她低着头,湿漉漉的头发黏在苍白的脸颊上,几片未化的雪花缀在发间。
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同样破旧的小包袱,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身体在寒冷和恐
惧中微微颤抖,像一片寒风中的枯叶。
「柳娘,快,快见过曹孝廉!这可是桥太尉举荐的贵人!」老吏在一旁催促,
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那名叫柳娘的女子浑身一颤,猛地抬起头。
一张脸生得倒是清秀,眉眼间还残留着几分稚气,只是此刻写满了惊惶与无
助。
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如同受惊的小鹿,随即又死死垂下头,膝盖一
软就要跪下去,声音细若蚊蚋,带着浓重的哭腔:「奴…奴婢柳娘,见…见过孝
廉郎…」
「抬起头来。」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穿透力,盖过了窗外
的风雪声。
柳娘身体又是一抖,迟疑着,极其缓慢地抬起脸。
昏黄的灯光下,她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嘴唇被冻得发紫,微微哆嗦着。
那双眼睛很大,此刻蓄满了泪水,水光潋滟,却盛满了惊惧和一种近乎绝望
的哀恳。
她不敢与我对视,目光躲闪着,最终落在我腰间的剑柄上,身体抖得更厉害
了。
「孝廉郎您瞧,柳娘可是正经的『官记』,身子清白着呢!」老吏在一旁谄
笑着,忽然一步上前,动作粗鲁地抓住柳娘纤细的右臂,猛地将她的旧袄袖子向
上捋起,直捋到肘弯处!
「啊!」柳娘猝不及防,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下意识地拼命挣扎,想抽回
手臂。
但那老吏的手如同铁钳,她哪里挣得脱?
一截欺霜赛雪的纤细小臂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下。
肌肤细腻,在寒冷中激起一层细小的粟粒。
而在那靠近肘弯内侧的雪白肌肤上,赫然一点殷红,形如朱砂,鲜艳夺目!
守宫砂!
老吏得意地指着那点刺目的红:「您瞧!货真价实!这可是宫里…呃,官里
都验看过的!若非今日大雪,又逢孝廉郎您这样的贵人,这等『清倌人』轻易还
不拿出来呢!」
他唾沫横飞地夸耀着,仿佛在展示一件稀奇的货物。
柳娘停止了徒劳的挣扎,整个人如同被抽去了骨头,瘫软下来。
她不再看任何人,只是死死盯着自己臂上那点象征「贞洁」的朱砂,大颗大
颗的泪珠无声地滚落,砸在冰冷的地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那泪水中蕴含的屈辱、恐惧和认命,浓得化不开。
守宫砂?清白?在这宦官当道、指鹿为马、连渤海王都能阖族屠戮的雒阳?
看着那点刺目的殷红,再看着柳娘眼中死灰般的绝望,白日里王甫车驾的熏香、
缇骑的鞭影、囚徒颈上的枷锁、孩童的哭嚎…无数画面瞬间冲入脑海,与眼前这
「官中体己」的「清白」形成最尖锐、最荒诞的讽刺!
一股暴戾的火焰「腾」地在我胸中炸开!什么狗屁贞烈!什么狗屁清白!在
这污浊透顶的世道里,不过是权势者手中随意把玩、随意撕碎的玩物!就像那渤
海王阖族的性命,就像这洛水驿中瑟瑟发抖的「官妓」!
「呵…」一声冰冷的嗤笑从我喉间溢出,带着浓重的嘲讽与一种近乎毁灭的
欲望。
「宦官当道,贞烈何用?」我的目光如同实质的冰锥,刺向老吏,也刺向柳
娘臂上那点可笑的朱砂。
老吏脸上的谄笑瞬间僵住,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般反应,眼中闪过一丝错愕
和不安。
而柳娘,在听到「宦官当道,贞烈何用」八个字时,身体猛地一颤,抬起泪
眼,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那眼神中,除了恐惧,竟第一次闪过一丝极微弱的、难以言喻的震动。
我不再看那老吏,目光如饿狼般锁住柳娘,声音低沉而危险,带着不容置疑
的命令:「你,留下。他,滚出去。」
老吏如蒙大赦,又似心有不甘地瞥了柳娘一眼,终究不敢违逆,连声应着
「是,是」,佝偻着身子飞快地退了出去,还「贴心」地掩上了那扇吱呀作响的
破门。
门扉合拢的刹那,狭小的厢房内,只剩下炭盆微弱的噼啪声、窗外鬼哭般的
风雪呜咽,以及我和眼前这瑟瑟发抖的猎物。
空气仿佛凝固了,弥漫着劣质炭烟、霉味、劣酒气,还有柳娘身上传来的、
一丝极淡的、属于年轻女子的、混合着皂角和恐惧的微涩气息。
我站起身,高大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投下巨大的阴影,瞬间将柳娘完全笼
罩。
她如同被猛兽盯上的小兔,惊恐地后退一步,脊背重重撞在冰冷的土墙上,
退无可退。
怀中的破旧包袱「啪」地掉在地上,几件同样破旧的衣物散落出来。
「不…不要…」她摇着头,泪水汹涌而出,声音破碎不成调,双手下意识地
紧紧环抱住自己,仿佛这样就能抵御即将到来的厄运。
我一步步逼近,靴子踩在坑洼不平的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步都像
踩在她的心尖上。
白日里在朱雀阙前压抑的滔天怒火,目睹王甫暴行却无法发作的憋屈,对这
腐朽世道刻骨的憎恶,还有那被「守宫砂」彻底点燃的、想要撕碎一切虚伪的暴
戾欲望,此刻如同熔岩般在血管里奔涌咆哮!我需要宣泄!需要征服!需要在这
最卑微的角落,用最原始的方式,宣告我对这狗屁世道的蔑视与践踏!
「嗤啦——!」
一声布帛撕裂的脆响,猛地撕裂了室内的死寂!我甚至懒得去解那粗糙的衣
结,大手抓住柳娘身上那件单薄的旧袄前襟,猛地向两边一扯!脆弱的粗布如同
纸片般应声而裂,露出里面同样破旧、打着补丁的白色中衣,以及那骤然暴露在
冰冷空气中、因恐惧和寒冷而剧烈起伏的、尚未完全发育的纤细胸脯轮廓。
两点小巧的、淡粉色的乳尖在冰冷的刺激下瞬间挺立,如同受惊的花苞。
「啊——!」柳娘发出一声凄厉到变调的尖叫,那声音里充满了极致的惊恐
和羞耻,刺得人耳膜生疼。
她像被烙铁烫到一般,双手疯狂地想要掩住破碎的衣襟,身体拼命地扭动挣
扎,双腿胡乱踢蹬。
「放开我!求求你!大人!孝廉郎!放过奴婢吧!」她哭喊着,涕泪横流,
绝望的哀求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
然而,这微弱的反抗在我绝对的力量面前,如同蚍蜉撼树。
我一手如铁钳般轻易地攥住她两只纤细的手腕,猛地反剪到她身后,用一只
大手就牢牢锁住。
她的挣扎瞬间被禁锢,整个人被我死死地按在了冰冷粗糙的土墙上!冰冷的
土墙激得她又是一阵剧烈的颤抖,赤裸的胸脯被迫紧贴着冰冷刺骨的墙面,那两
点挺立的蓓蕾被粗糙的土粒摩擦,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和更深的羞耻。
「贞烈?」我俯身,灼热的、带着浓重酒气的呼吸喷在她冰凉汗湿的颈侧,
声音低沉沙哑,如同恶魔的低语,每一个字都淬着冰冷的毒液和灼热的欲望。
「在这雒阳城里,连龙子凤孙的命都贱如草芥!你这点『清白』…算个什么
东西?」说话间,另一只手已毫不留情地探下,粗暴地扯开了她腰间同样破旧的
布带,连同那单薄的中裤,一并撕扯下来!
冰冷的空气瞬间侵袭了她下身最隐秘的肌肤,柳娘的身体猛地绷紧,如同离
水的鱼,所有的哭喊和哀求都卡在了喉咙里,只剩下绝望到极致的、破碎的呜咽。
她徒劳地扭动着被禁锢的身体,双腿试图并拢,却被我强横地分开。
少女最私密的花园被迫暴露在昏黄的灯光和男人灼热的目光下,稀疏柔软的
耻毛下,是紧紧闭合、因恐惧而微微抽搐的粉嫩肉缝。
窗外,北风卷着雪沫,疯狂地撞击着窗棂,发出如同野兽咆哮般的呜咽,与
室内女子压抑的、濒死般的悲鸣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曲残酷的乐章。
昏黄的灯光在墙壁上投下两个剧烈晃动的、扭曲纠缠的影子。
我没有任何温存,没有半分怜惜。
白日里那囚徒颈上枷锁的沉重、孩童眼中凝固的恐惧、宦官脸上那令人作呕
的得意,还有那弥漫不散的血腥与熏香混合的怪味…这一切都化作了最原始的、
毁灭性的力量。
我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凶兽,只想用最粗暴的方式,撕碎眼前所能触及的一
切「干净」与「体面」,在这最卑贱的角落,完成一次对那至高无上却又肮脏透
顶的雒阳宫阙的亵渎与宣战!
腾出的那只手,粗暴地揉捏着她胸前那对尚显青涩的椒乳,力道之大,让那
柔软的乳肉在指缝间变形,淡粉的乳尖被搓揉得充血挺立,带来一阵阵尖锐的刺
痛。
柳娘的身体在我掌下剧烈地颤抖,呜咽声更加破碎,泪水混合着汗水,在她
苍白的小脸上肆意流淌。
我的身体紧紧贴着她被迫撅起的臀,隔着衣物,能清晰感受到那根早已被怒
火和欲望烧灼得坚硬如铁的阳物,正凶悍地顶在她赤裸的臀缝间,隔着薄薄的布
料,研磨着那紧闭的、微微湿润的入口。
那滚烫的硬度和充满侵略性的顶弄,让柳娘浑身僵直,恐惧达到了顶点。
「不…不要…那里…求您…」她语无伦次地哀求着,身体因极度的恐惧而筛
糠般抖动。
「由不得你!」我低吼一声,如同宣判。
那只在她下身肆虐的手,猛地探入她被迫分开的双腿之间,粗糙的手指带着
不容抗拒的力道,强行挤开那两片因紧张而紧紧闭合的、柔嫩湿滑的阴唇,直接
刺入那从未被外物侵入过的、紧致滚烫的甬道入口!
「啊——!」一声撕心裂肺、不似人声的惨嚎从柳娘喉咙深处迸发出来!那
是一种肉体被强行撕裂、灵魂被瞬间洞穿的剧痛!她的身体猛地向上弓起,如同
被拉满的弓弦,随即又重重地砸回冰冷的土墙,剧烈的痉挛从被侵犯的私处瞬间
蔓延至全身!双腿间,一股温热的、带着处子特有腥甜气息的鲜血,顺着她被迫
分开的大腿内侧,蜿蜒流下,在昏黄的灯光下,刺目惊心!
那根强行闯入的手指,清晰地感受到了处女膜的破裂和甬道内壁因剧痛而引
发的疯狂痉挛与绞紧。
那紧致、滚烫、带着撕裂伤口的触感,混合着指尖沾染的温热滑腻的处子之
血,如同最强烈的春药,彻底点燃了我体内那头名为「毁灭」的凶兽!
我猛地抽出手指,带出一缕黏腻的血丝。
另一只禁锢她双手的手也骤然松开。
柳娘如同被抽掉了所有骨头,软软地顺着墙壁滑倒在地,蜷缩成一团,双手
死死捂住剧痛的下体,身体因剧痛和极致的恐惧而剧烈抽搐,发出断断续续、如
同濒死小兽般的哀鸣。
但这并非结束,仅仅是开始。
我俯身,抓住她纤细的脚踝,如同拖拽一件没有生命的货物,粗暴地将她拖
离冰冷的墙角,拖向那张散发着霉味和汗腥气的土炕。
她的身体在冰冷粗糙的泥地上摩擦,留下淡淡的血痕和泪水的湿迹。
将她甩上那张铺着肮脏草席的土炕,我甚至没有完全褪下自己的下裳,只是
粗暴地扯开腰带,将那早已怒张贲起、青筋虬结的粗长阳物释放出来。
那狰狞的凶器在昏黄的灯光下昂然挺立,顶端分泌的粘液在火光中闪烁着淫
靡的光泽。
我分开她因剧痛和恐惧而无力并拢的双腿,将自己沉重的身躯压了上去。
膝盖强硬地顶开她试图保护自己的手臂,将那还在流血、微微抽搐的粉嫩肉
穴彻底暴露在眼前。
那撕裂的伤口,那混合着处子血和爱液的湿滑泥泞,散发着一种令人疯狂的、
禁忌的腥甜气息。
没有任何前戏,没有任何缓冲。
我腰身猛地一沉,用尽全身的力气,将胯下那根滚烫坚硬的凶器,对准那刚
刚被手指强行开拓、还在流血颤抖的稚嫩穴口,狠狠地、一捅到底!
「呃啊——!」
比刚才更加凄厉、更加绝望的惨叫声,几乎要掀翻这破败的屋顶!柳娘的身
体如同被利刃贯穿,猛地向上弹起,双眼瞬间翻白,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
同破风箱般的抽气声,随即又重重地砸回草席,整个人如同被钉在砧板上的鱼,
只剩下无意识的、剧烈的痉挛和抽搐。
我的阳物被一种难以想象的、极致紧窄滚烫的肉壁死死包裹、绞紧!那紧致
感,那被撕裂的嫩肉带来的摩擦感,那温热的处子之血如同润滑剂般包裹着茎身
的滑腻感…所有的一切,都汇聚成一股灭顶的、摧毁理智的快感洪流,瞬间冲垮
了所有的堤坝!
「呃…!」我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双手死死掐住她纤细的腰肢,将她牢
牢固定在身下,开始了一场毫无怜悯、只有纯粹征服与毁灭的狂暴挞伐!
粗长的阳物在那紧窄湿滑、饱受蹂躏的肉穴里疯狂地抽插!每一次凶狠的贯
穿,都直捣花心最深处,顶开那稚嫩的宫口,带来柳娘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哀鸣和
身体剧烈的抽搐。
每一次猛烈的抽出,都带出大量混合着鲜血和爱液的粘稠白沫,溅落在肮脏
的草席和她赤裸的小腹、大腿上。
「痛…好痛…大人…饶了奴婢…求您…饶了…」柳娘的声音已经嘶哑得不成
样子,只剩下破碎的、不成调的哀求和哭泣。
她的身体在剧烈的撞击下无助地晃动,纤细的腰肢几乎要被折断,胸前那对
青涩的椒乳随着撞击而上下抛动,乳尖早已红肿不堪。
她的眼神彻底涣散,失去了焦距,只剩下无边的痛苦和绝望,泪水如同决堤
般涌出。
而我,完全沉浸在这暴虐的征服之中。
白日里所有的愤怒、憋屈、憎恶,都化作了胯下最原始的力量,通过这狂暴
的抽插,狠狠地贯入这具象征着「官中体面」的、被「守宫砂」标记的年轻肉体!
看着她痛苦扭曲的脸,听着她绝望的哀鸣,感受着那紧窄肉穴在剧痛和蹂躏下无
助的痉挛和绞紧…一种前所未有的、扭曲而强烈的快感,如同毒液般流遍全身!
「贞洁?清白?狗屁!」
我一边狂暴地挺动着腰胯,让粗硬的阳物在那饱受摧残的肉穴里横冲直撞,
一边喘息着,在她耳边发出低沉的、如同诅咒般的话语,「王甫杀得了渤海王,
老子就破得了你这『官妓』的身子!这世道…就是用来操的!」
说话间,我猛地抓住她一只纤细的手腕,强行拽到她的脸侧,让她那沾满泪
水和尘土的手指,触碰到自己臂弯处那点早已被汗水、泪水和摩擦弄得模糊不清、
甚至沾上了点点血污的守宫砂!
「看看!看看你这点『干净』!现在…还干净吗?!」我狞笑着,腰下的撞
击更加凶狠,每一次都顶得她身体向上耸动,发出沉闷的肉体撞击声。
柳娘的手指触碰到那象征着屈辱和毁灭的印记,身体猛地一颤,随即爆发出
最后一声凄厉到极致的哀嚎,如同灵魂被彻底撕裂。
她头一歪,竟直接昏死了过去。
但这并未让我停止。
征服的快感如同燎原的野火,烧灼着每一寸神经。
我继续在她失去意识的身体上狂暴地驰骋,感受着那紧窄肉穴在昏迷中依旧
本能的、无意识的收缩和绞紧,反而带来一种别样的、亵渎死物般的刺激。
粗硬的阳物在那泥泞不堪、混合着血与蜜的甬道里疯狂进出,带出更多粘稠
的汁液,将两人交合的下体弄得一片狼藉。
不知过了多久,一股强烈的、如同火山喷发般的酥麻感从尾椎骨直冲头顶!
我低吼一声,腰眼一麻,滚烫浓稠的阳精如同开闸的洪水,猛烈地喷射而出,一
股股地狠狠灌入那被蹂躏得红肿不堪、微微外翻的稚嫩花心深处!滚烫的精液冲
击着脆弱的宫口,让昏迷中的柳娘身体也本能地一阵剧烈抽搐。
我伏在她汗湿冰冷的身体上,剧烈地喘息着,感受着高潮的余韵在四肢百骸
流窜,也感受着身下这具肉体微弱的生命气息。
体内那股狂暴的戾气随着精液的喷射,似乎暂时得到了平息,但并未消失,
只是沉潜下去,化作一种更深沉、更冰冷的东西,沉淀在眼底。
白日里雒阳城的血腥与黑暗,并未因这场暴行而远离,反而更加清晰地烙印
在脑海。
破败的土炕上,铺着一张散发着霉味和汗腥气的草席。
柳娘如同被狂风暴雨彻底摧折碾碎的残花,瘫软其上,身体还在无法控制地
微微抽搐。
破碎的粗布衣衫凌乱地散落在冰冷的泥地上,像褪下的蛇皮。
她双目紧闭,脸色死灰,脸上泪痕交错,嘴唇被自己咬破,渗出血丝,混合
着屈辱的唾液。
臂弯处,那点曾经鲜艳的守宫砂,早已在粗暴的碾压、汗水和血污的浸染下
彻底模糊,只留下一片刺目的、带着血丝的淤红和擦伤,如同一个被彻底戳破、
踩进泥里的谎言。
她赤裸的下身一片狼藉,大腿内侧布满青紫的指痕和摩擦的血痕,腿间那处
粉嫩的秘处此刻红肿外翻,如同被蹂躏过的花瓣,混合着暗红的处子之血、粘稠
的爱液和大量浓白的精液,正缓缓地、一股股地顺着她微微分开的大腿根部流淌
下来,浸湿了身下肮脏的草席,散发出浓烈的、情欲与暴力混合的腥膻气息。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情欲宣泄后的腥膻气息,混杂着劣质炭火的烟味、霉
味,令人窒息。
我翻身坐起,赤着上身,胸膛剧烈起伏,汗水顺着贲张的肌肉线条滑落。
随手抓起炕头那半壶冰冷的劣酒,仰头灌下。
辛辣的液体冲刷着喉咙,却冲不散心头那沉甸甸的块垒。
目光扫过草席上如同破碎人偶般的柳娘,她死灰般的脸色和腿间那一片狼藉
的惨状,像一根刺,扎在方才那短暂的、建立在毁灭之上的快感里。
没有征服后的餍足,只有一种更深的、冰冷的空虚,以及对这世道更刻骨的
厌憎。
我起身,衣物摩擦发出窸窣的声响。
柳娘的身体随着这声音猛地一颤,眼皮微微颤动,似乎从昏迷的边缘被惊醒,
发出一声细微的、如同受伤小兽般的呜咽,身体下意识地蜷缩起来,双臂紧紧抱
住自己赤裸的、布满青紫的胸脯。
没有再看她。
我走到那散落着破旧衣物的泥地旁,从随身的行囊里摸出几枚沉甸甸的五铢
钱。
冰冷的铜钱在掌心掂了掂,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然后,手腕一抖,几枚铜钱带着破空声,精准地、带着一种近乎羞辱的力道,
叮叮当当地砸落在柳娘赤裸的、布满青紫指痕和精液污迹的小腹上,冰冷的触感
激得她又是一阵剧烈的瑟缩。
「拿着。」我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冷硬,听不出任何情绪,仿佛刚才那场暴
风骤雨从未发生。
「你的『清白』钱。」
柳娘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紧闭的眼角再次溢出大颗的泪珠。
她没有动,只是那呜咽声更加压抑、更加绝望了。
我穿戴整齐,系好佩剑,玄色的大氅重新披上肩头,将方才的一切疯狂与不
堪都掩藏其下。
拉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门,一股裹挟着雪沫的凛冽寒风猛地灌入,吹得炭盆
里的火星一阵乱飞,也吹得草席上赤裸的柳娘又是一阵剧烈的瑟缩和咳嗽。
门外,风雪依旧肆虐,天地间一片苍茫混沌。
老吏佝偻的身影不知何时已候在廊下阴暗处,见我出来,脸上立刻堆起那熟
悉的、世故而卑微的笑容,搓着手迎上一步:「孝廉郎…可还…满意?」
我没有回答,甚至没有看他一眼。
目光越过他佝偻的肩头,投向风雪弥漫的远方。
在那片混沌的尽头,雒阳城巨大的、如同蛰伏巨兽般的轮廓,在灰暗的天幕
下若隐若现。
白日里立于朱雀阙前的誓言,带着血腥与情欲的余温,在心底轰然回响,比
这洛水的寒风更加刺骨,更加灼热:此间宫阙,当染吾色!
(第一卷:初据兖州第一章结束)
2025.08.28首发于第一会所
字数:10832
写在开篇:
【边看边学?这才是男人该追的历史小说!】
【尘封史册之外,曹阿瞒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魏武猎艳录》是情色小说,亦是严肃历史。
本书以《三国志》、《后汉书》为骨,以合理想象为血肉,深入汉末宫廷与
战场,力图还原一个全面、立体、有血有肉的曹操。
他的霸业与他的欲望,本就一体两面,共同谱写了这段传奇。
在这里,您不仅能见证官渡的烽火、赤壁的东风,更能窥见金市的珠喉、帐
中的温存。
这一切,都是理解那个时代与那个人的钥匙。
读稗官野史,习正经国史。
一部小说,双重收获。
【本故事为闲余创作、额外连载,更新与否,皆在诸君之间。若您喜爱,恳
请点赞、评论。助力,点赞越多,更新越快!诸公,请助孟德一臂之力!】
【历史背景导读(建宁七年冬,公元174年,洛阳城外)】
皇帝:此时的皇帝是东汉的汉灵帝刘宏。
他是个贪图享乐、昏庸无能的皇帝,非常信任和依赖身边的宦官(太监)。
宦官集团:以王甫、曹节为首的一群大太监,把持着朝政大权。
他们权势熏天,陷害忠良,卖官鬻爵,无恶不作。
皇帝对他们言听计从。
受害者:士大夫(清流官员与太学生):许多正直的官员和读书人(太学生)
痛恨宦官祸国殃民,被称为「清流」或「党人」。
他们试图铲除宦官,但失败了。
关键事件:大约6年前(公元168年,建宁元年),大将军窦武(外戚,皇帝
的岳父)和太傅陈蕃(德高望重的老臣)这两位清流领袖,联合起来谋划诛杀王
甫、曹节等宦官。
可惜计划泄露,窦武、陈蕃反被宦官诬陷谋反,惨遭杀害,他们的家族也被
灭门。
这就是震惊天下的「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开始。
此后,宦官对清流的迫害就没停过。
曹操此刻:曹操(字孟德),当时只有20岁。
他的家乡在谯郡(今安徽亳州)。
他被当地官府推举为「孝廉」(汉代选拔官员的一种资格)。
他带着一位重要官员——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桥玄的推荐信,刚刚抵达
帝国首都洛阳的郊外。
他怀揣着年轻人的热血和抱负,准备踏入这个由宦官掌控、危机四伏的政治
中心寻找机会。
正文开始
第一卷:初据兖州 第一章:洛水寒刃
【建宁七年(174年)冬,洛阳城外】
曹操以孝廉身入京,持太尉桥玄荐书,冀入仕途。
是时,宦官(王甫、曹节等)势炽,权倾朝野。
雒阳城的风似裹了冰碴子,抽在脸上生疼。
我勒马洛水桥头,玄色大氅灌满了北风,猎猎作响。
桥玄公的荐书在怀中滚烫,孝廉之名,不过踏入这龙潭虎穴的敲门砖罢了。
抬眼望去,雒阳城阙如蹲伏的巨兽,灰蒙蒙的宫墙压在天际,透着一股子陈
腐的腥气。
「孟德,雒阳水深,慎之,再慎之。」桥公临别之言犹在耳畔。
我曹孟德年方二十,血是热的,骨是硬的,岂惧这潭浑水?嘴角扯出一丝冷
峭,靴跟一磕马腹,乌骓马长嘶一声,踏碎洛水薄冰,直向那帝国心脏奔去。
甫入城,血腥气便混着尘土味扑面而来。
朱雀大街不复传闻中冠盖云集,反倒透着一股死寂。
行人瑟缩,商户半掩门板,唯有一队队执戟的北军士卒,甲胄森然,踏着整
齐而沉重的步伐巡弋而过,铁靴踏在青石板上,发出令人心悸的闷响。
他们的眼神,鹰隼般扫过街巷,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压迫。
「闪开!王常侍车驾!」尖利如阉鸡的嗓音骤然撕裂沉闷。
街面瞬间清空,人群如潮水般惶恐退避,匍匐于道旁。
我勒马避入巷口阴影,冷眼看去。
只见数十名身着绛红缇骑服的宦官亲卫开道,簇拥着一辆金顶朱轮、饰以鸾
鸟的奢华安车,车帘低垂,看不清内里人物,唯有一股浓烈得刺鼻的熏香弥漫开
来。
车驾之后,竟拖曳着长长一串囚徒!男女老幼皆有,粗麻囚衣褴褛,颈套重
枷,脚系铁镣,在寒风中踉跄前行,每一步都留下暗红的血印。
鞭子如毒蛇般不时抽下,皮开肉绽的闷响和压抑的哀嚎令人齿冷。
「渤海王刘悝谋逆,奉旨,阖族弃市!」一个领头宦官趾高气扬地宣告,声
音里透着残忍的快意。
渤海王刘悝?先帝亲弟!我心头剧震,一股寒意从脊椎直冲头顶。
谋逆?何等荒谬!不过是王甫、曹节这些阉竖清除异己的惯用伎俩!看着那
些被拖向刑场、面如死灰的宗室贵胄,看着他们眼中孩童懵懂的恐惧和妇人绝望
的泪水,我攥着缰绳的手背青筋暴起,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这就是我大汉的雒阳?这就是我立志要匡扶的朝堂?金碧辉煌的宫阙之下,
流淌的竟是如此肮脏腥臭的血!
「嗬…嗬…」一个白发老翁踉跄跌倒,枷锁砸地,发出刺耳的声响。
旁边一名缇骑狞笑着扬起鞭子,眼看就要落下。
「住手!」一声断喝自我喉中迸出,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
乌骓马受惊,前蹄扬起,长嘶震耳。
那缇骑的鞭子顿在半空,连同周围所有目光,齐刷刷射向巷口阴影中的我。
惊疑、审视、还有一丝被冒犯的阴鸷。
领头的宦官眯起细长的眼,上下打量着我这风尘仆仆的外乡人,嘴角扯出一
个皮笑肉不笑的弧度:「哪来的狂徒?敢阻王常侍法驾?活腻了不成?」他尖细
的嗓音像钝刀刮过骨头。
我深吸一口凛冽的寒气,压下翻腾的杀意,在马上略一拱手,声音沉冷如铁:
「谯县曹操,蒙桥太尉举为孝廉,初入京师。见老弱踉跄,一时情急,惊扰常侍,
还望海涵。」
「桥玄」二字,被我刻意咬得清晰。
那宦官听到「桥玄」名号,眼中阴鸷稍敛,但倨傲不减,冷哼一声:「哼,
原来是桥太尉举荐的孝廉郎。年轻人,雒阳城的水,深着呢。管好你的嘴,还有
…你的手!走!」
他不再看我,尖声催促队伍。
鞭子终究没再落下,但那老翁也被粗暴地拖拽而起,留下一道更长的血痕。
车驾与囚队在压抑的死寂中继续前行,唯有铁链拖地的哗啦声,如同地狱的
丧钟,一下下敲在人心上。
夕阳如血,将巍峨的南宫门阙染成一片凄厉的暗红。
我驻马朱雀阙前,望着那象征着至高皇权的巨大门楼,白日里那囚徒颈上枷
锁的沉重、孩童眼中凝固的恐惧、宦官脸上那令人作呕的得意,还有那弥漫不散
的血腥与熏香混合的怪味,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啃噬着我的心脏。
「此间宫阙…」我低声呢喃,声音被寒风撕碎。
一股比洛水更刺骨的寒意,混杂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灼烧肺腑的野望,在胸
中疯狂滋长。
这金玉其外的煌煌帝都,内里早已是蛆虫横行的腐肉。
桥公的「慎之」言犹在耳,但此刻,我只觉一股暴戾之气直冲顶门。
慎?在这虎狼之地,唯有权柄与力量,才是活命、才是主宰的法则!我要撕
开这层虚伪的锦绣,我要…染指这至高的权色!
「当染吾色!」最后四字,如同从牙缝中挤出的铁屑,带着血腥的决绝。
指甲深深掐入掌心,刺痛传来,却远不及心头那团烈火的万分之一。
暮色四合,风雪更急。
我按着驿丞的指点,策马出了雒阳南门,沿着覆满薄雪的官道行了约莫半个
时辰,才在洛水一处荒僻河湾旁,寻到那处破败的官驿。
几间土坯房在风雪中瑟缩,门前一盏气死风灯昏黄摇曳,仿佛随时会被寒风
掐灭。
驿卒是个佝偻的老吏,须发皆白,脸上沟壑纵横,堆着世故又卑微的笑,将
我迎入唯一一间还算完整的厢房。
「曹孝廉受累了,受累了!这雒阳城里的驿馆,早被那些个…咳,贵人们塞
满了,只能委屈您在这城外将就一宿。」老吏一边哈着腰解释,一边麻利地拨弄
着屋内一个呛人的炭盆,试图驱散那刺骨的阴冷。
土炕冰凉,墙角结着蛛网,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劣质炭火的烟气。
「无妨。」我解下大氅,随手扔在炕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目光扫过这陋室,白日里朱雀阙前的滔天怒火与野望,此刻被这现实的破败
与寒冷一激,反而沉淀下来,化作一种更沉郁、更尖锐的东西,在胸中左冲右突,
亟待宣泄。
案上有一壶劣酒,我抓过来,拔掉塞子,仰头灌了一大口。
辛辣的液体如同火线滚入喉中,灼烧着冰冷的脏腑,却压不住那股邪火。
老吏察言观色,浑浊的老眼在我年轻却紧绷的脸上转了几圈,又瞥了一眼我
腰间佩剑,脸上那卑微的笑容里,忽然掺进一丝心照不宣的暧昧。
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带着浓重的市井气:「孝廉郎初来乍到,白日里又
受了惊,这长夜漫漫,天寒地冻的…可需寻个暖脚的,解解乏气,驱驱晦气?」
我握着酒壶的手一顿,抬眼看他,目光锐利如刀。
老吏被我看得心头一凛,腰弯得更低,却仍陪着笑:「小老儿不敢欺瞒,这
驿馆虽破,却也…咳咳,备着些『官中』的体己。
都是干净人儿,懂规矩,知冷暖。」他特意加重了「官中」二字,手指隐晦
地朝雒阳城方向指了指。
官妓?王甫、曹节那些阉狗爪牙掌控下的玩物?白日里那奢华安车中飘出的
浓烈熏香,与眼前这破败驿馆的霉味、劣酒的辛辣,还有老吏口中「干净人儿」
的暗示,奇异地交织在一起,猛地在我心头点燃了一把邪火。
一种强烈的、近乎亵渎的冲动涌了上来——撕碎这虚伪的「干净」,践踏这
由阉竖把持的所谓「官中」体面!
「哦?」
我放下酒壶,声音听不出喜怒,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剑柄,「唤来。」
老吏如蒙大赦,脸上褶子都笑开了花:「好嘞!孝廉郎稍待,稍待!」
他佝偻着身子,飞快地退了出去,脚步声消失在呼啸的风雪声中。
屋内重归死寂,唯有炭盆里偶尔爆出几点火星,映着我阴晴不定的脸。
窗外,北风卷着雪沫,疯狂地拍打着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嘶鸣。
约莫一炷香后,门轴发出艰涩的「吱呀」声。
老吏推开门,一股更猛烈的寒气裹着雪花卷入。
他侧身让开,一个单薄的身影被推了进来,随即门又被迅速关上。
来人是个女子,约莫十六七岁年纪,身形纤细,裹着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
丁的粗布旧袄,下摆短了一截,露出冻得发青的纤细脚踝。
她低着头,湿漉漉的头发黏在苍白的脸颊上,几片未化的雪花缀在发间。
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同样破旧的小包袱,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身体在寒冷和恐
惧中微微颤抖,像一片寒风中的枯叶。
「柳娘,快,快见过曹孝廉!这可是桥太尉举荐的贵人!」老吏在一旁催促,
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那名叫柳娘的女子浑身一颤,猛地抬起头。
一张脸生得倒是清秀,眉眼间还残留着几分稚气,只是此刻写满了惊惶与无
助。
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如同受惊的小鹿,随即又死死垂下头,膝盖一
软就要跪下去,声音细若蚊蚋,带着浓重的哭腔:「奴…奴婢柳娘,见…见过孝
廉郎…」
「抬起头来。」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穿透力,盖过了窗外
的风雪声。
柳娘身体又是一抖,迟疑着,极其缓慢地抬起脸。
昏黄的灯光下,她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嘴唇被冻得发紫,微微哆嗦着。
那双眼睛很大,此刻蓄满了泪水,水光潋滟,却盛满了惊惧和一种近乎绝望
的哀恳。
她不敢与我对视,目光躲闪着,最终落在我腰间的剑柄上,身体抖得更厉害
了。
「孝廉郎您瞧,柳娘可是正经的『官记』,身子清白着呢!」老吏在一旁谄
笑着,忽然一步上前,动作粗鲁地抓住柳娘纤细的右臂,猛地将她的旧袄袖子向
上捋起,直捋到肘弯处!
「啊!」柳娘猝不及防,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下意识地拼命挣扎,想抽回
手臂。
但那老吏的手如同铁钳,她哪里挣得脱?
一截欺霜赛雪的纤细小臂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下。
肌肤细腻,在寒冷中激起一层细小的粟粒。
而在那靠近肘弯内侧的雪白肌肤上,赫然一点殷红,形如朱砂,鲜艳夺目!
守宫砂!
老吏得意地指着那点刺目的红:「您瞧!货真价实!这可是宫里…呃,官里
都验看过的!若非今日大雪,又逢孝廉郎您这样的贵人,这等『清倌人』轻易还
不拿出来呢!」
他唾沫横飞地夸耀着,仿佛在展示一件稀奇的货物。
柳娘停止了徒劳的挣扎,整个人如同被抽去了骨头,瘫软下来。
她不再看任何人,只是死死盯着自己臂上那点象征「贞洁」的朱砂,大颗大
颗的泪珠无声地滚落,砸在冰冷的地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那泪水中蕴含的屈辱、恐惧和认命,浓得化不开。
守宫砂?清白?在这宦官当道、指鹿为马、连渤海王都能阖族屠戮的雒阳?
看着那点刺目的殷红,再看着柳娘眼中死灰般的绝望,白日里王甫车驾的熏香、
缇骑的鞭影、囚徒颈上的枷锁、孩童的哭嚎…无数画面瞬间冲入脑海,与眼前这
「官中体己」的「清白」形成最尖锐、最荒诞的讽刺!
一股暴戾的火焰「腾」地在我胸中炸开!什么狗屁贞烈!什么狗屁清白!在
这污浊透顶的世道里,不过是权势者手中随意把玩、随意撕碎的玩物!就像那渤
海王阖族的性命,就像这洛水驿中瑟瑟发抖的「官妓」!
「呵…」一声冰冷的嗤笑从我喉间溢出,带着浓重的嘲讽与一种近乎毁灭的
欲望。
「宦官当道,贞烈何用?」我的目光如同实质的冰锥,刺向老吏,也刺向柳
娘臂上那点可笑的朱砂。
老吏脸上的谄笑瞬间僵住,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般反应,眼中闪过一丝错愕
和不安。
而柳娘,在听到「宦官当道,贞烈何用」八个字时,身体猛地一颤,抬起泪
眼,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那眼神中,除了恐惧,竟第一次闪过一丝极微弱的、难以言喻的震动。
我不再看那老吏,目光如饿狼般锁住柳娘,声音低沉而危险,带着不容置疑
的命令:「你,留下。他,滚出去。」
老吏如蒙大赦,又似心有不甘地瞥了柳娘一眼,终究不敢违逆,连声应着
「是,是」,佝偻着身子飞快地退了出去,还「贴心」地掩上了那扇吱呀作响的
破门。
门扉合拢的刹那,狭小的厢房内,只剩下炭盆微弱的噼啪声、窗外鬼哭般的
风雪呜咽,以及我和眼前这瑟瑟发抖的猎物。
空气仿佛凝固了,弥漫着劣质炭烟、霉味、劣酒气,还有柳娘身上传来的、
一丝极淡的、属于年轻女子的、混合着皂角和恐惧的微涩气息。
我站起身,高大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投下巨大的阴影,瞬间将柳娘完全笼
罩。
她如同被猛兽盯上的小兔,惊恐地后退一步,脊背重重撞在冰冷的土墙上,
退无可退。
怀中的破旧包袱「啪」地掉在地上,几件同样破旧的衣物散落出来。
「不…不要…」她摇着头,泪水汹涌而出,声音破碎不成调,双手下意识地
紧紧环抱住自己,仿佛这样就能抵御即将到来的厄运。
我一步步逼近,靴子踩在坑洼不平的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步都像
踩在她的心尖上。
白日里在朱雀阙前压抑的滔天怒火,目睹王甫暴行却无法发作的憋屈,对这
腐朽世道刻骨的憎恶,还有那被「守宫砂」彻底点燃的、想要撕碎一切虚伪的暴
戾欲望,此刻如同熔岩般在血管里奔涌咆哮!我需要宣泄!需要征服!需要在这
最卑微的角落,用最原始的方式,宣告我对这狗屁世道的蔑视与践踏!
「嗤啦——!」
一声布帛撕裂的脆响,猛地撕裂了室内的死寂!我甚至懒得去解那粗糙的衣
结,大手抓住柳娘身上那件单薄的旧袄前襟,猛地向两边一扯!脆弱的粗布如同
纸片般应声而裂,露出里面同样破旧、打着补丁的白色中衣,以及那骤然暴露在
冰冷空气中、因恐惧和寒冷而剧烈起伏的、尚未完全发育的纤细胸脯轮廓。
两点小巧的、淡粉色的乳尖在冰冷的刺激下瞬间挺立,如同受惊的花苞。
「啊——!」柳娘发出一声凄厉到变调的尖叫,那声音里充满了极致的惊恐
和羞耻,刺得人耳膜生疼。
她像被烙铁烫到一般,双手疯狂地想要掩住破碎的衣襟,身体拼命地扭动挣
扎,双腿胡乱踢蹬。
「放开我!求求你!大人!孝廉郎!放过奴婢吧!」她哭喊着,涕泪横流,
绝望的哀求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
然而,这微弱的反抗在我绝对的力量面前,如同蚍蜉撼树。
我一手如铁钳般轻易地攥住她两只纤细的手腕,猛地反剪到她身后,用一只
大手就牢牢锁住。
她的挣扎瞬间被禁锢,整个人被我死死地按在了冰冷粗糙的土墙上!冰冷的
土墙激得她又是一阵剧烈的颤抖,赤裸的胸脯被迫紧贴着冰冷刺骨的墙面,那两
点挺立的蓓蕾被粗糙的土粒摩擦,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和更深的羞耻。
「贞烈?」我俯身,灼热的、带着浓重酒气的呼吸喷在她冰凉汗湿的颈侧,
声音低沉沙哑,如同恶魔的低语,每一个字都淬着冰冷的毒液和灼热的欲望。
「在这雒阳城里,连龙子凤孙的命都贱如草芥!你这点『清白』…算个什么
东西?」说话间,另一只手已毫不留情地探下,粗暴地扯开了她腰间同样破旧的
布带,连同那单薄的中裤,一并撕扯下来!
冰冷的空气瞬间侵袭了她下身最隐秘的肌肤,柳娘的身体猛地绷紧,如同离
水的鱼,所有的哭喊和哀求都卡在了喉咙里,只剩下绝望到极致的、破碎的呜咽。
她徒劳地扭动着被禁锢的身体,双腿试图并拢,却被我强横地分开。
少女最私密的花园被迫暴露在昏黄的灯光和男人灼热的目光下,稀疏柔软的
耻毛下,是紧紧闭合、因恐惧而微微抽搐的粉嫩肉缝。
窗外,北风卷着雪沫,疯狂地撞击着窗棂,发出如同野兽咆哮般的呜咽,与
室内女子压抑的、濒死般的悲鸣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曲残酷的乐章。
昏黄的灯光在墙壁上投下两个剧烈晃动的、扭曲纠缠的影子。
我没有任何温存,没有半分怜惜。
白日里那囚徒颈上枷锁的沉重、孩童眼中凝固的恐惧、宦官脸上那令人作呕
的得意,还有那弥漫不散的血腥与熏香混合的怪味…这一切都化作了最原始的、
毁灭性的力量。
我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凶兽,只想用最粗暴的方式,撕碎眼前所能触及的一
切「干净」与「体面」,在这最卑贱的角落,完成一次对那至高无上却又肮脏透
顶的雒阳宫阙的亵渎与宣战!
腾出的那只手,粗暴地揉捏着她胸前那对尚显青涩的椒乳,力道之大,让那
柔软的乳肉在指缝间变形,淡粉的乳尖被搓揉得充血挺立,带来一阵阵尖锐的刺
痛。
柳娘的身体在我掌下剧烈地颤抖,呜咽声更加破碎,泪水混合着汗水,在她
苍白的小脸上肆意流淌。
我的身体紧紧贴着她被迫撅起的臀,隔着衣物,能清晰感受到那根早已被怒
火和欲望烧灼得坚硬如铁的阳物,正凶悍地顶在她赤裸的臀缝间,隔着薄薄的布
料,研磨着那紧闭的、微微湿润的入口。
那滚烫的硬度和充满侵略性的顶弄,让柳娘浑身僵直,恐惧达到了顶点。
「不…不要…那里…求您…」她语无伦次地哀求着,身体因极度的恐惧而筛
糠般抖动。
「由不得你!」我低吼一声,如同宣判。
那只在她下身肆虐的手,猛地探入她被迫分开的双腿之间,粗糙的手指带着
不容抗拒的力道,强行挤开那两片因紧张而紧紧闭合的、柔嫩湿滑的阴唇,直接
刺入那从未被外物侵入过的、紧致滚烫的甬道入口!
「啊——!」一声撕心裂肺、不似人声的惨嚎从柳娘喉咙深处迸发出来!那
是一种肉体被强行撕裂、灵魂被瞬间洞穿的剧痛!她的身体猛地向上弓起,如同
被拉满的弓弦,随即又重重地砸回冰冷的土墙,剧烈的痉挛从被侵犯的私处瞬间
蔓延至全身!双腿间,一股温热的、带着处子特有腥甜气息的鲜血,顺着她被迫
分开的大腿内侧,蜿蜒流下,在昏黄的灯光下,刺目惊心!
那根强行闯入的手指,清晰地感受到了处女膜的破裂和甬道内壁因剧痛而引
发的疯狂痉挛与绞紧。
那紧致、滚烫、带着撕裂伤口的触感,混合着指尖沾染的温热滑腻的处子之
血,如同最强烈的春药,彻底点燃了我体内那头名为「毁灭」的凶兽!
我猛地抽出手指,带出一缕黏腻的血丝。
另一只禁锢她双手的手也骤然松开。
柳娘如同被抽掉了所有骨头,软软地顺着墙壁滑倒在地,蜷缩成一团,双手
死死捂住剧痛的下体,身体因剧痛和极致的恐惧而剧烈抽搐,发出断断续续、如
同濒死小兽般的哀鸣。
但这并非结束,仅仅是开始。
我俯身,抓住她纤细的脚踝,如同拖拽一件没有生命的货物,粗暴地将她拖
离冰冷的墙角,拖向那张散发着霉味和汗腥气的土炕。
她的身体在冰冷粗糙的泥地上摩擦,留下淡淡的血痕和泪水的湿迹。
将她甩上那张铺着肮脏草席的土炕,我甚至没有完全褪下自己的下裳,只是
粗暴地扯开腰带,将那早已怒张贲起、青筋虬结的粗长阳物释放出来。
那狰狞的凶器在昏黄的灯光下昂然挺立,顶端分泌的粘液在火光中闪烁着淫
靡的光泽。
我分开她因剧痛和恐惧而无力并拢的双腿,将自己沉重的身躯压了上去。
膝盖强硬地顶开她试图保护自己的手臂,将那还在流血、微微抽搐的粉嫩肉
穴彻底暴露在眼前。
那撕裂的伤口,那混合着处子血和爱液的湿滑泥泞,散发着一种令人疯狂的、
禁忌的腥甜气息。
没有任何前戏,没有任何缓冲。
我腰身猛地一沉,用尽全身的力气,将胯下那根滚烫坚硬的凶器,对准那刚
刚被手指强行开拓、还在流血颤抖的稚嫩穴口,狠狠地、一捅到底!
「呃啊——!」
比刚才更加凄厉、更加绝望的惨叫声,几乎要掀翻这破败的屋顶!柳娘的身
体如同被利刃贯穿,猛地向上弹起,双眼瞬间翻白,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
同破风箱般的抽气声,随即又重重地砸回草席,整个人如同被钉在砧板上的鱼,
只剩下无意识的、剧烈的痉挛和抽搐。
我的阳物被一种难以想象的、极致紧窄滚烫的肉壁死死包裹、绞紧!那紧致
感,那被撕裂的嫩肉带来的摩擦感,那温热的处子之血如同润滑剂般包裹着茎身
的滑腻感…所有的一切,都汇聚成一股灭顶的、摧毁理智的快感洪流,瞬间冲垮
了所有的堤坝!
「呃…!」我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双手死死掐住她纤细的腰肢,将她牢
牢固定在身下,开始了一场毫无怜悯、只有纯粹征服与毁灭的狂暴挞伐!
粗长的阳物在那紧窄湿滑、饱受蹂躏的肉穴里疯狂地抽插!每一次凶狠的贯
穿,都直捣花心最深处,顶开那稚嫩的宫口,带来柳娘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哀鸣和
身体剧烈的抽搐。
每一次猛烈的抽出,都带出大量混合着鲜血和爱液的粘稠白沫,溅落在肮脏
的草席和她赤裸的小腹、大腿上。
「痛…好痛…大人…饶了奴婢…求您…饶了…」柳娘的声音已经嘶哑得不成
样子,只剩下破碎的、不成调的哀求和哭泣。
她的身体在剧烈的撞击下无助地晃动,纤细的腰肢几乎要被折断,胸前那对
青涩的椒乳随着撞击而上下抛动,乳尖早已红肿不堪。
她的眼神彻底涣散,失去了焦距,只剩下无边的痛苦和绝望,泪水如同决堤
般涌出。
而我,完全沉浸在这暴虐的征服之中。
白日里所有的愤怒、憋屈、憎恶,都化作了胯下最原始的力量,通过这狂暴
的抽插,狠狠地贯入这具象征着「官中体面」的、被「守宫砂」标记的年轻肉体!
看着她痛苦扭曲的脸,听着她绝望的哀鸣,感受着那紧窄肉穴在剧痛和蹂躏下无
助的痉挛和绞紧…一种前所未有的、扭曲而强烈的快感,如同毒液般流遍全身!
「贞洁?清白?狗屁!」
我一边狂暴地挺动着腰胯,让粗硬的阳物在那饱受摧残的肉穴里横冲直撞,
一边喘息着,在她耳边发出低沉的、如同诅咒般的话语,「王甫杀得了渤海王,
老子就破得了你这『官妓』的身子!这世道…就是用来操的!」
说话间,我猛地抓住她一只纤细的手腕,强行拽到她的脸侧,让她那沾满泪
水和尘土的手指,触碰到自己臂弯处那点早已被汗水、泪水和摩擦弄得模糊不清、
甚至沾上了点点血污的守宫砂!
「看看!看看你这点『干净』!现在…还干净吗?!」我狞笑着,腰下的撞
击更加凶狠,每一次都顶得她身体向上耸动,发出沉闷的肉体撞击声。
柳娘的手指触碰到那象征着屈辱和毁灭的印记,身体猛地一颤,随即爆发出
最后一声凄厉到极致的哀嚎,如同灵魂被彻底撕裂。
她头一歪,竟直接昏死了过去。
但这并未让我停止。
征服的快感如同燎原的野火,烧灼着每一寸神经。
我继续在她失去意识的身体上狂暴地驰骋,感受着那紧窄肉穴在昏迷中依旧
本能的、无意识的收缩和绞紧,反而带来一种别样的、亵渎死物般的刺激。
粗硬的阳物在那泥泞不堪、混合着血与蜜的甬道里疯狂进出,带出更多粘稠
的汁液,将两人交合的下体弄得一片狼藉。
不知过了多久,一股强烈的、如同火山喷发般的酥麻感从尾椎骨直冲头顶!
我低吼一声,腰眼一麻,滚烫浓稠的阳精如同开闸的洪水,猛烈地喷射而出,一
股股地狠狠灌入那被蹂躏得红肿不堪、微微外翻的稚嫩花心深处!滚烫的精液冲
击着脆弱的宫口,让昏迷中的柳娘身体也本能地一阵剧烈抽搐。
我伏在她汗湿冰冷的身体上,剧烈地喘息着,感受着高潮的余韵在四肢百骸
流窜,也感受着身下这具肉体微弱的生命气息。
体内那股狂暴的戾气随着精液的喷射,似乎暂时得到了平息,但并未消失,
只是沉潜下去,化作一种更深沉、更冰冷的东西,沉淀在眼底。
白日里雒阳城的血腥与黑暗,并未因这场暴行而远离,反而更加清晰地烙印
在脑海。
破败的土炕上,铺着一张散发着霉味和汗腥气的草席。
柳娘如同被狂风暴雨彻底摧折碾碎的残花,瘫软其上,身体还在无法控制地
微微抽搐。
破碎的粗布衣衫凌乱地散落在冰冷的泥地上,像褪下的蛇皮。
她双目紧闭,脸色死灰,脸上泪痕交错,嘴唇被自己咬破,渗出血丝,混合
着屈辱的唾液。
臂弯处,那点曾经鲜艳的守宫砂,早已在粗暴的碾压、汗水和血污的浸染下
彻底模糊,只留下一片刺目的、带着血丝的淤红和擦伤,如同一个被彻底戳破、
踩进泥里的谎言。
她赤裸的下身一片狼藉,大腿内侧布满青紫的指痕和摩擦的血痕,腿间那处
粉嫩的秘处此刻红肿外翻,如同被蹂躏过的花瓣,混合着暗红的处子之血、粘稠
的爱液和大量浓白的精液,正缓缓地、一股股地顺着她微微分开的大腿根部流淌
下来,浸湿了身下肮脏的草席,散发出浓烈的、情欲与暴力混合的腥膻气息。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情欲宣泄后的腥膻气息,混杂着劣质炭火的烟味、霉
味,令人窒息。
我翻身坐起,赤着上身,胸膛剧烈起伏,汗水顺着贲张的肌肉线条滑落。
随手抓起炕头那半壶冰冷的劣酒,仰头灌下。
辛辣的液体冲刷着喉咙,却冲不散心头那沉甸甸的块垒。
目光扫过草席上如同破碎人偶般的柳娘,她死灰般的脸色和腿间那一片狼藉
的惨状,像一根刺,扎在方才那短暂的、建立在毁灭之上的快感里。
没有征服后的餍足,只有一种更深的、冰冷的空虚,以及对这世道更刻骨的
厌憎。
我起身,衣物摩擦发出窸窣的声响。
柳娘的身体随着这声音猛地一颤,眼皮微微颤动,似乎从昏迷的边缘被惊醒,
发出一声细微的、如同受伤小兽般的呜咽,身体下意识地蜷缩起来,双臂紧紧抱
住自己赤裸的、布满青紫的胸脯。
没有再看她。
我走到那散落着破旧衣物的泥地旁,从随身的行囊里摸出几枚沉甸甸的五铢
钱。
冰冷的铜钱在掌心掂了掂,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然后,手腕一抖,几枚铜钱带着破空声,精准地、带着一种近乎羞辱的力道,
叮叮当当地砸落在柳娘赤裸的、布满青紫指痕和精液污迹的小腹上,冰冷的触感
激得她又是一阵剧烈的瑟缩。
「拿着。」我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冷硬,听不出任何情绪,仿佛刚才那场暴
风骤雨从未发生。
「你的『清白』钱。」
柳娘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紧闭的眼角再次溢出大颗的泪珠。
她没有动,只是那呜咽声更加压抑、更加绝望了。
我穿戴整齐,系好佩剑,玄色的大氅重新披上肩头,将方才的一切疯狂与不
堪都掩藏其下。
拉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门,一股裹挟着雪沫的凛冽寒风猛地灌入,吹得炭盆
里的火星一阵乱飞,也吹得草席上赤裸的柳娘又是一阵剧烈的瑟缩和咳嗽。
门外,风雪依旧肆虐,天地间一片苍茫混沌。
老吏佝偻的身影不知何时已候在廊下阴暗处,见我出来,脸上立刻堆起那熟
悉的、世故而卑微的笑容,搓着手迎上一步:「孝廉郎…可还…满意?」
我没有回答,甚至没有看他一眼。
目光越过他佝偻的肩头,投向风雪弥漫的远方。
在那片混沌的尽头,雒阳城巨大的、如同蛰伏巨兽般的轮廓,在灰暗的天幕
下若隐若现。
白日里立于朱雀阙前的誓言,带着血腥与情欲的余温,在心底轰然回响,比
这洛水的寒风更加刺骨,更加灼热:此间宫阙,当染吾色!
(第一卷:初据兖州第一章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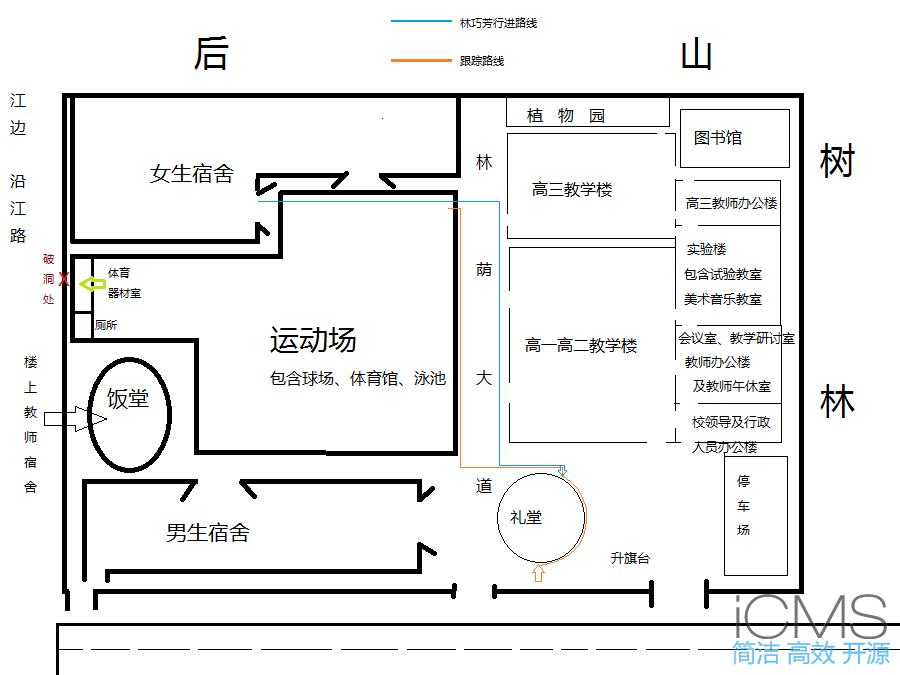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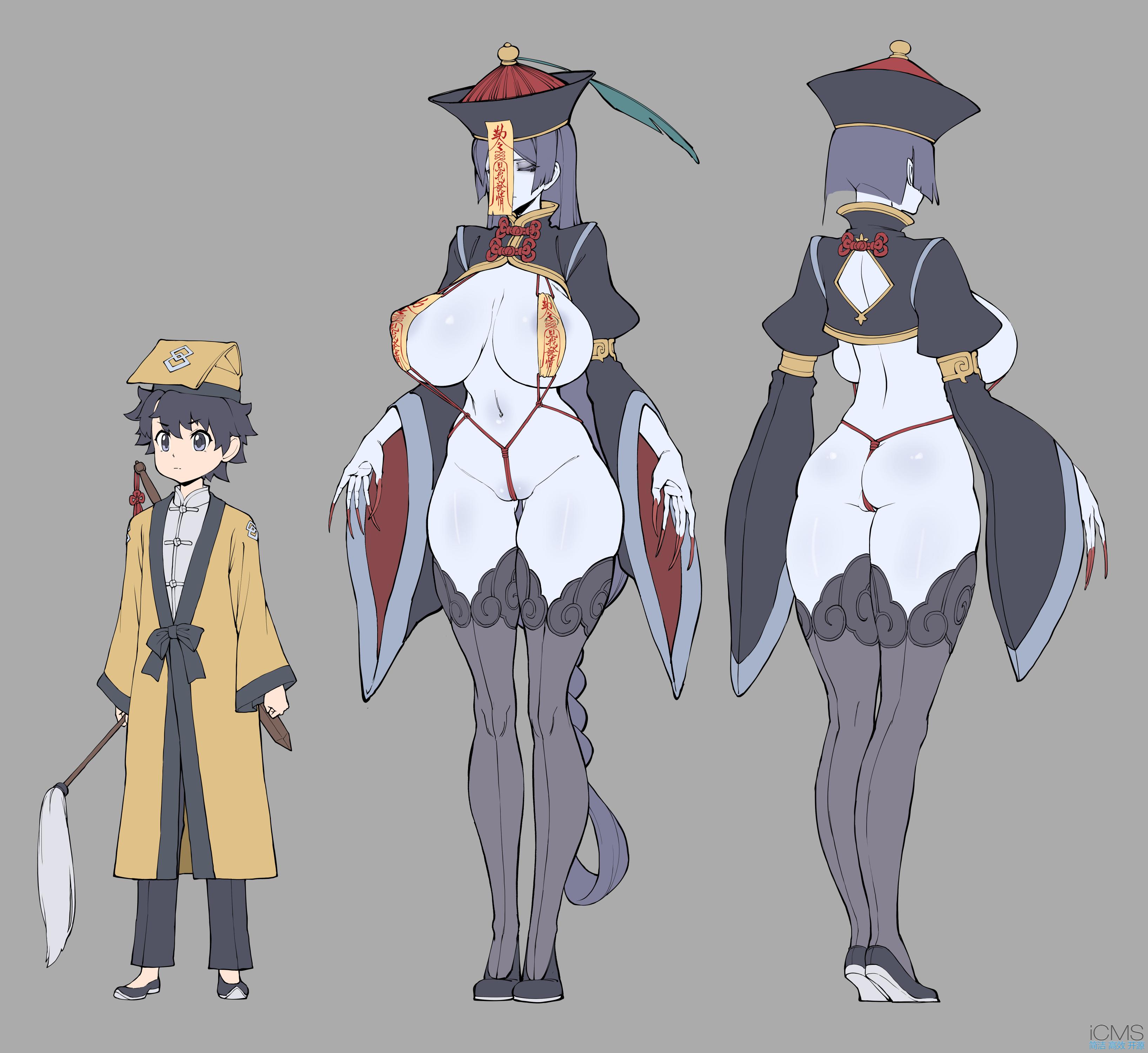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